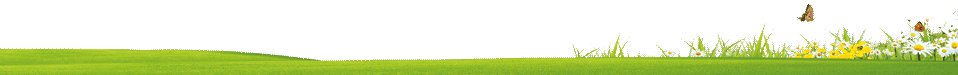别让性别成为人生的坟墓
《公民与性别(citizens-gender)》
发刊词
一个人能改变什么呢?
也许能改变世界,也许什么也改变不了。但对于多数人来说,至少可以尝试着改变自己。
“尝试”是一个很奇妙的词语,它提供了无限的可能,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无论中外,“尝试”总是一段艰难的历程。性别,由于与性相关,与吃饭和生存的紧迫性等位,因此,对性别的尝试尤其困难。
不论是中世纪的欧洲,宗教对女性的性压迫,还是古代中国,性藉由道德和伦理,对女性的统治,都触目惊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不仅是女人,男人也被“强制”地赋予种类繁多的思想、行动枷锁。
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有社会的地方就有统治与被统治,强势与弱势,而性别就依借这样的逻辑被建构,被规训,被定格,而“性”作为一种生存必需品,像食物一样被争夺,被奴役,被剥削。
性别对于一些人无异于坟墓。
那是谁把性别变成了坟墓?又是谁窃取了性?
1981年12月1日,美国确诊了第一例艾滋病例,随后艾滋病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迅速从一个医学话题延伸到人际关系、社会伦理、性等方方面面。当艾滋病被认为与“性”有关后,禁欲主义者很快增多,人们有充足理由相信只有禁欲,不发生性关系,才会是安全的,因为在艾滋病不能治疗的年代,感染等于死亡。
但就像古希腊丢失了贞操的圣女一样,人们发现性的压抑是如此困难,人们一方面对那些能真正禁欲的人投之以敬意,另一方面,一些人开始埋怨禁欲的不人道。
事实证明,艾滋病也阻挡不了性,禁欲的方法失效了,因为性似乎是不能禁止的。但艾滋病成功地将性别异化了,妓女成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艾滋病通过“性”向人们输出了“淫荡”,那些性放荡的人有了新的标签。同性恋者也被认为是艾滋病的代名词,受到鄙视和打压。
然而,性别终究没有因为艾滋病变成坟墓,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人们发现,面对艾滋病,所有人是一样的,一个人并不会因为属于某个群体而有太多不同,个体的选择和行为似乎更为关键。但是性别确实曾经进入过坟墓,性别的异化仍然在不断上演。
那些非主流的性、性别往往被视为异端,性的欲望,性别的表现,在社会压力下扭曲,一个个双面,甚至多面人,被塑造出来,熟人社会中的模样,陌生人社会中的模样,白天的模样与夜晚的模样,表现出极大的差异。
性原本是内生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理体验,性格、性趣、性象作为性的外化,则往往受到生理诉求和社会规则的双重影响,但遗憾的是,一些人在他者的标准下,变身他者的影子,完全抛弃了自身的生理诉求,对自身的性别属性改头换面,以新的方式继续着性压抑和性别的扭曲。
这样的性别是不是坟墓呢?
个体有个体的追求,这种主体性探索旁人很难触及,但社会是群体的社会,个人又难以避免受到社会的影响。但问题是,社会有没有给个体表达的空间和权利。在古代,“三纲五常”作为强加给中国女性的枷锁,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伦理和道德基础,除了个别女性,这种社会规约牢不可破。
而公民社会强调尊重个体的权利,倡导平等,更大程度地给予人们表达自身诉求的环境,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共识,从逻辑上讲,也给了性别认同以更宽松的环境。
但性别对于一些人来说,仍然是坟墓,因为他们放弃了尝试表达的机会,亲手消灭了人生的无限可能性,这无疑是悲哀的。
要知道,古今中外,那些被称为爱情典范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无一不是在冲破性别世俗枷锁的模式下,被人们所认知和纪念的,而在性别背后,还有经济、权势、地位和家庭等多种固有模式的突破,确实发人深思。
一个人能改变什么呢?至少不让性别成为自己人生的坟墓吧。
《公民与性别(citizens-gender)》愿与大家一起寻找真正的性别自我。
长按二维码,关注《公民与性别》
|
顶一下
|
- 深圳男同约会纠纷,何以成了娱乐事件? 2014-12-24
- 库克出柜了,中国的同志名人何时站出来? 2014-12-24
- 同性恋公益机构,“你们很敏感!” 2014-12-24
- 专栏:警惕公益圈内部歧视问题 2014-05-30
- 同性恋电影审查越来越宽松? 2014-11-01
- 资料:求同存异和求异存同:同性婚姻的宪法之纬 2014-12-31
-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理分析 2014-12-31
- 当同性恋来访者遇到咨询师的“价值中立” 2015-01-30
- 为了心中的彩虹 2014-05-28
- 阿强:“拒绝同性恋机构注册”缘于缺乏常识 2014-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