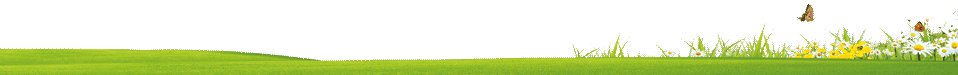直同微刊第8期 | 是歧视还是自由言论?
“我喜欢瘦的,不喜欢胖的”,“我不会找胖子做男朋友”,“我不会和非处女在一起”,“我不喜欢同性恋”,“我觉得女人当不了一个好领导”。
以上表述中,哪些属于自由言论,哪些属于歧视?当我们听到一些言论,既像“表达个人的喜好”,又似乎有歧视某个群体的意味时,怎样才能做出判断?
这要看这种言论有没有妨害到你所评价的人群的相应权利。
以“我不会和非处女在一起”为例:如果仅是个人持有的择偶标准,没有散播不利于非处女群体择偶的言论,没有妨碍到非处女群体的择偶,就不构成法律或道德层面上的歧视,而是该个体的择偶自由。一个人想找什么样的人做自己的伴侣,自愿缩小自己的择偶范围,这的确是他的权利。他不选非处女在一起,我们可以从审美层面去批评他,但不能强行要求他娶个非处,否则这也是越权。
但如果一个人说“非处女不能找伴侣”,并且还利用其身份地位在其管辖范围施行“非处女不能找伴侣”的决策;或者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在公开场合传播这种观念,妨害非处女群体通过正常渠道寻找伴侣的机会,就明显构成了歧视。
是否妨害当事人的权利,是区分歧视与言论自由的首要判据。可能有反对同性恋的人士会说,“既然同性恋要求我们接受他们的存在,那他们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反对同性恋的人存在呢”。这种表面上双方都在要求言论自由的说法实际上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同性恋的存在并没有妨害“反同”人士的正当权利,而“反同”人士的“反同”言行,却真实妨害了同性恋个人和群体的权利——例如最基本的生存权。
如果一个人说“我讨厌美女”,他并不能损害这个世界上任何美女的任何权利,大家听到不过哈哈一笑。而假如这个人是某个公司的高层,他认为美女都是草包,禁止职业资质合格的美女进入公司或获得平等的晋升机会,此时则构成歧视。这个例子不仅对女人成立,对同性恋、有色人种、或其他任何群体都是成立的。
在判断歧视时,还应尽量避免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与个人主观情感的影响。例如,当有人非议 “美女” 时,我们可能会觉得这并非歧视,而是出于嫉妒;但如果有人开“丑女”的玩笑,我们则可能易于将这种表达解读为歧视。实际上,是否构成歧视,与社会、个人对“美女”或“丑女”的认知方式无关。伤害到了“美女”群体权益的言论也有可能构成歧视;没有伤害到“丑女”的言论可能是说话者的自由。换言之,我们判断一个言论是否构成歧视,不应出于对言论来源的成见,也不应出于对言论所指向群体(无论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的同情。
此外,有时表面上没有影响力的言论,实际上却为歧视的滋生埋下了种子。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的表达,常常都带有“寻求认同最大化”的潜在动机。一个人说“我不喜欢同性恋”,也许并不是在单纯地表达他个人的喜好,也同时在表达他取得听者认同的愿望。这种表达中“寻求同伴,扩散价值观”的色彩多过“仅仅表达一下个人好恶”。因而这种表达也就超出了私人言论的范畴。从这个层面上看,防微杜渐地、适度地批评这种“准自由言论”是必要的。抛开法律或道德层面上的指责,可以退一步从审美层面做出评价,例如指出这是一种排他的审美取向或狭隘的价值观等等。度如何把控,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矫枉过正、乱扣帽子的那种批评,也要警惕。
综上所述,辨别歧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衡量说话者的影响力、决策权与言论动机,也要衡量言论对象群体的权益是否受到了真实的损害。语言本身并没有歧视或追求自由的意图,却有可能成为传播这些意图的媒介。
立场和版权声明:本文为直同道合《直同微刊》栏目特别约稿,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组织立场。尊重劳动,维护版权。未经授权,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违者必究。

|
顶一下
|
- 深圳男同约会纠纷,何以成了娱乐事件? 2014-12-24
- 库克出柜了,中国的同志名人何时站出来? 2014-12-24
- 同性恋公益机构,“你们很敏感!” 2014-12-24
- 专栏:警惕公益圈内部歧视问题 2014-05-30
- 同性恋难道不能做公益吗? 2014-06-25
- 同性恋电影审查越来越宽松? 2014-11-01
- 资料:求同存异和求异存同:同性婚姻的宪法之纬 2014-12-31
-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理分析 2014-12-31
- 资料:同性婚姻与我何干? 2014-12-31
- 当同性恋来访者遇到咨询师的“价值中立” 2015-01-30